晚饭后的厨房还飘着红烧肉的香气,我把最后一只碗放进消毒柜,“咔嗒”一声落了锁。客厅里却只有键盘清脆的敲击声,像支停不下来的快节奏舞曲,男友陈默窝在沙发里,后背弓成一张拉满的弓,眼睛死死黏在屏幕上,连我擦着手走出来都没抬一下。
“我去倒垃圾。”我晃了晃手里的垃圾袋,声音不大不小,刚好能盖过游戏里的音效。陈默头也不回地“嗯”了一声,手指在键盘上又是一阵翻飞,屏幕上跳出“双杀”的提示音,他兴奋地拍了下大腿,嘴角都快咧到耳根。我无奈地摇摇头,这副模样我早已习惯,只要一沾上游戏,他就像被按下了屏蔽键,天塌下来都比不上他的兵线重要。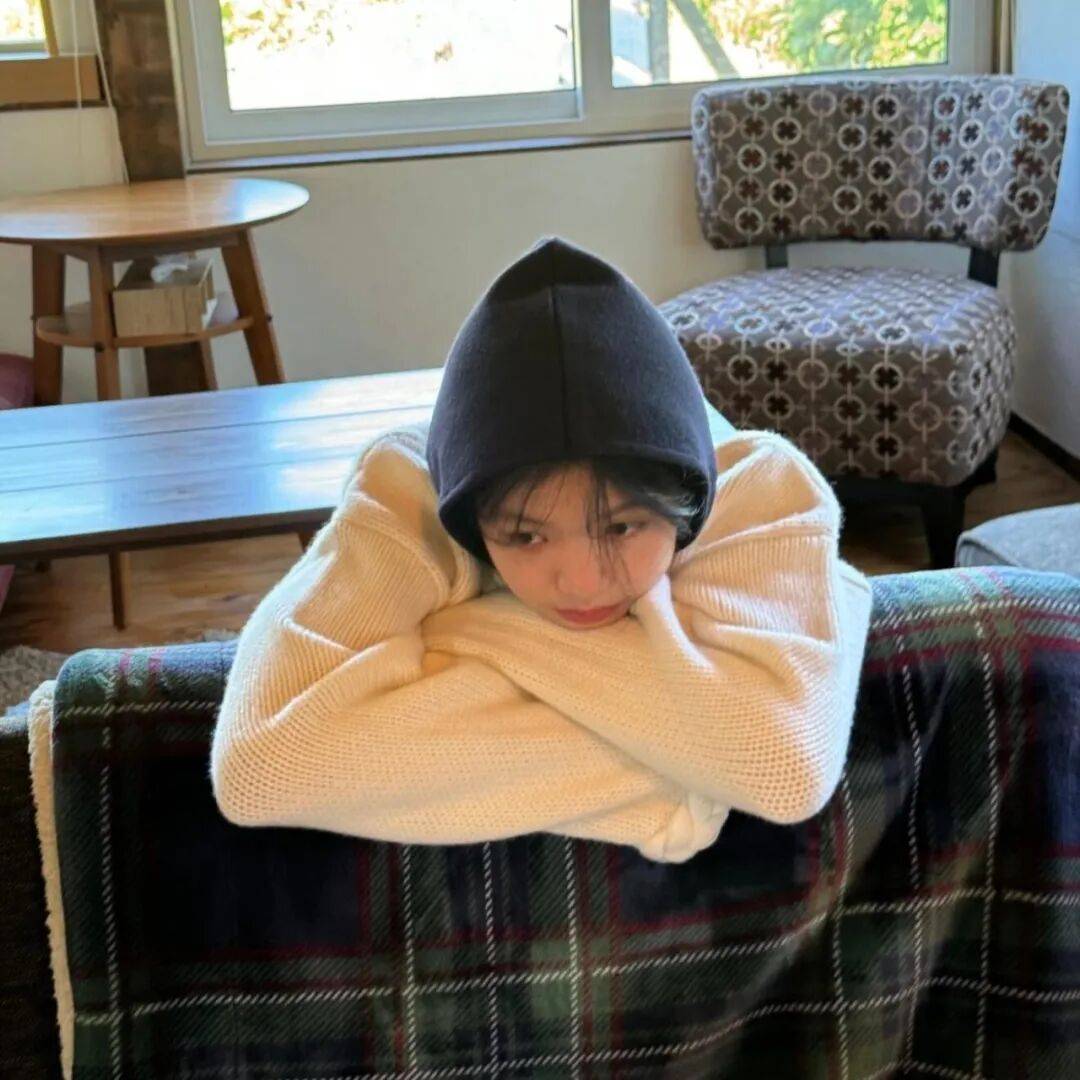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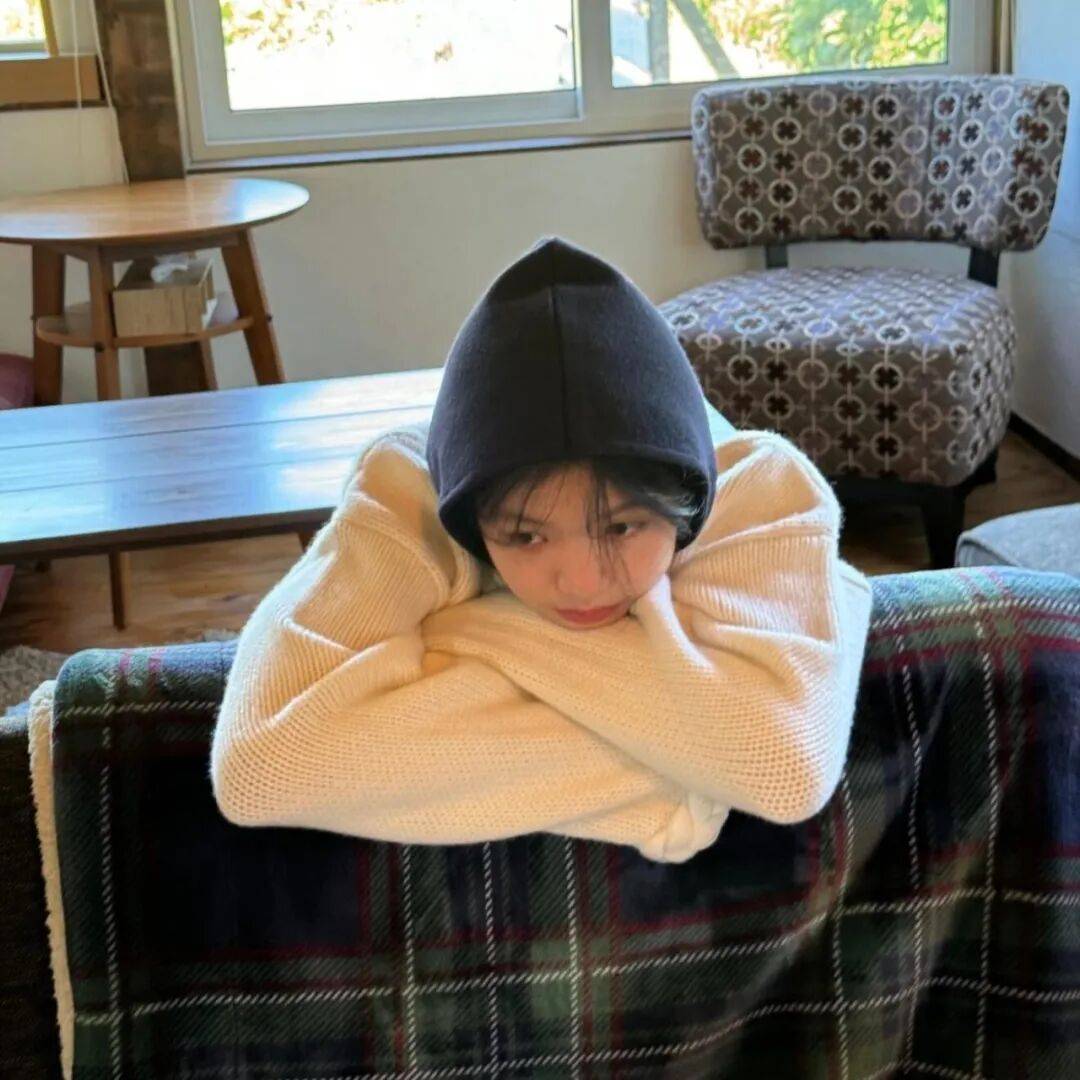
走到玄关换鞋时,墙上的挂钟刚好指向七点整。那是去年我们一起挑的复古挂钟,金属指针走起来“滴答滴答”的,像在数着流逝的时光。我盯着指针看了两秒,一个调皮的念头突然冒了出来。我踮着脚凑过去,轻轻捏住分针,一点一点往后拨,金属齿轮在指尖发出细微的摩擦声,直到指针稳稳停在十点的位置,才满意地拍了拍手。
楼下的垃圾分类站就在单元门口,我把垃圾袋分门别类投好,又在便利店买了支他爱喝的冰可乐,慢悠悠地往回走。晚风带着夏末的凉意,吹得路边的梧桐叶沙沙作响,我掏出手机刷了几条短视频,算着时间差不多了,才晃悠着进了电梯。
刚打开家门,就听见客厅里又传来一阵激烈的音效。我故意“砰”地一声带上房门,把可乐往玄关柜上一放,径直冲进客厅,声音瞬间拔高八度:“陈默!你看看都几点了!还在这儿玩游戏?”
陈默的手指猛地一顿,屏幕上的英雄应声倒地,他皱着眉转头:“怎么了这是?我马上就打完这局——”话没说完,他的目光扫过墙上的挂钟,瞳孔突然一缩。我清楚地看见他喉结滚动了一下,整个人像被烫到似的从沙发上弹了起来,键盘被他带得差点摔在地上。
“我去!都十点了?”他抓着头发原地转了个圈,眼睛瞪得像铜铃,“你下楼倒个垃圾去了几个小时啊?去哪了?是不是半路被朋友拉去逛街了?电话也不接!”他一边说一边摸手机,手指慌乱地在屏幕上划着,眉头拧成了川字。
我强忍着笑,故意板着脸叉腰:“我倒垃圾能去哪?倒是你,说好了只玩一小时,现在都超时多久了?明天不用上班了?”陈默的脸瞬间涨红,像是做错事的小学生,挠着头支支吾吾:“我……我没注意时间,这局打得太投入了。”他快步走到我身边,拉着我的手腕晃了晃,语气里满是讨好,“对不起嘛,我这就关电脑,马上就关。”

看着他手忙脚乱关游戏的样子,我终于忍不住笑出了声,指了指墙上的挂钟:“你再仔细看看。”陈默疑惑地转头,盯着挂钟看了半天,突然反应过来,伸手挠了挠我的下巴:“好啊,你敢捉弄我?”他一把将我拉进怀里,假装生气地咬了咬我的耳垂,“说,是不是早就看我不顺眼了?”
我笑着从玄关柜上拿起冰可乐递给他:“谁让你玩游戏不理我。”陈默拉开拉环,冰凉的气泡涌了出来,他喝了一大口,然后把我搂得更紧:“我的错我的错,以后玩游戏定闹钟,保证随叫随到。”他低头看了眼手机,七点十五分的字样格外清晰,“不过说真的,你这招也太狠了,我差点以为自己要通宵了。”
客厅里的挂钟依旧“滴答”作响,月光透过窗帘洒进来,落在我们交握的手上。我靠在陈默怀里,听着他絮絮叨叨地保证以后会平衡游戏和生活,心里暖融融的。或许这就是爱情最真实的样子,没有轰轰烈烈的桥段,却藏在这些互相捉弄又彼此包容的小瞬间里,像那杯冰可乐,初尝带着点刺激,回味却满是甘甜。




